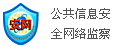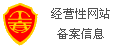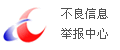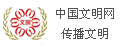張振華是華中農(nóng)業(yè)大學植物科學與技術學院“張之洞班”的在讀本科生。至今,他的母親仍然不太理解這個高考超出一本線58分的“讀書好苗子”,怎么就選擇了農(nóng)業(yè)大學,還回來和自己一樣務農(nóng)了。張振華則慶幸:還好沒有將戶口簽到學校,自己還保留農(nóng)村人的身份。
一邊上學,一邊在內(nèi)蒙古開展苜蓿草的種植事業(yè),張振華的生活,被劃分成田間地頭和教室實驗室兩部分:暑期農(nóng)忙,農(nóng)閑趕回學校復習考試。事實上,不少像張振華這樣從事農(nóng)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的大學生,往往根在農(nóng)村,受過高等教育,希望以新的思維來再造自己的家鄉(xiāng)。迎接他們的,是怎樣的挑戰(zhàn)?
農(nóng)民并沒有覺得大學生種地不靠譜
張振華小時候放過牛,知道過度放牧對草原的破壞。父親2012年開始養(yǎng)牛,張振華幫著購買牧草的時候,發(fā)現(xiàn)了苜蓿的寶貴。這種開著紫花、看似普通的草不僅蛋白質(zhì)含量豐富、再生性強,所含的豆科牧草根瘤菌固氮還能改善種植土壤的質(zhì)量。
他開始著手紫花苜蓿的生產(chǎn)。和傳統(tǒng)的種植方法不同,他采取的是機械化、規(guī)模化的模式,從播種到插秧都不需要太多人工。在內(nèi)蒙古呼和浩特市賽罕區(qū)和烏蘭察布市涼城縣,他的父親拿出畢生積蓄,支持他用于紫花苜蓿的種植。華中農(nóng)業(yè)大學拿出實驗田來,用于苜蓿新產(chǎn)品的試驗。
這個農(nóng)村孩子不怕吃苦,但是為苜蓿選種育種的時候,幾個小時的低頭勞作,還是讓他有些頭暈。他的導師、華中農(nóng)業(yè)大學教授趙劍提醒他:培育出最理想的種子,往往需要14年時間。農(nóng)業(yè)是個急不來的過程。
前期尋求資金的時候,張振華則遭遇了更多挑戰(zhàn)。農(nóng)村有農(nóng)村的文化,在家鄉(xiāng)內(nèi)蒙古,他和幾個潛在的投資人約在一起,八九個人喝掉了十幾瓶白酒也沒談成,張振華曾經(jīng)憤憤地想:不干了!
更大的挑戰(zhàn)在土地上。張振華的農(nóng)村戶口顯示出了優(yōu)勢,按照《農(nóng)村土地承包法》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(guī)定:“承包期內(nèi),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(qū)的市,轉(zhuǎn)為非農(nóng)業(yè)戶口的,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(fā)包方。承包方不交回的,發(fā)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。”也就是說,如果轉(zhuǎn)入武漢的非農(nóng)戶口,張振華需要以家庭的名義才能獲得承包土地。
但是,承包土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要實現(xiàn)大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,需要將小塊土地連接在一起。一開始,擁有土地的農(nóng)民并不看好這種奇怪的作物,挨家挨戶地進行說服工作很久。這兒三畝那兒兩畝難以集中,需要以土地換土地,才能將分散的土地集中,“土地是農(nóng)民的根本,這是一個各方協(xié)調(diào)的過程”。
最終,父子倆在涼城流轉(zhuǎn)了3000多畝土地。在呼和浩特市,1000多畝土地來自近60戶農(nóng)民。紫花苜蓿切中了市場需求,種植的第一季,苜蓿草就盈利了。僅2014年5月種下的1000多畝,就掙了100多萬元。
讓張振華欣慰的是,農(nóng)民們并沒有覺得一個大學生回來種地不靠譜。當?shù)氐霓r(nóng)村,務農(nóng)的年輕人已經(jīng)很少了,留守的多為50歲以上的中老年。他們希望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,能給自己帶來新的希望。
未來,張振華計劃采取農(nóng)業(yè)合作社的形勢,租賃農(nóng)民的土地,讓農(nóng)民用自己的技術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紫花苜蓿。
本網(wǎng)原創(chuàng),未經(jīng)許可,不得轉(zhuǎn)載。【注:凡注明“來源:XXX(非陜西教育信息網(wǎng) snedunews.cn)”的作品,均轉(zhuǎn)載自其它媒體,轉(zhuǎn)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網(wǎng)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;如因作品內(nèi)容、版權和其它問題需要同本網(wǎng)聯(lián)系的,請在30日內(nèi)進行。郵箱:553916702@qq.com】
必看
08 / 06月
08 / 06月
07 / 06月
09 / 06月
18 / 05月
25 / 04月
25 / 05月
07 / 06月
18 / 05月
07 / 06月
24 / 05月
19 / 05月
視頻
原創(chuàng)
標簽